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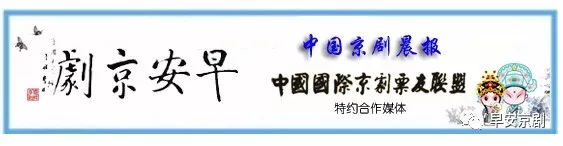
談戲曲劇本寫作,尤其是談論其中敘事與抒情手法的差異,離不開有關戲劇“動作”的理解。
從整體格局上看,所謂戲劇動作,指的不是普通意義上人物從心理到身體的行為,一個具有完整性的戲劇動作,更合適的解釋,是指在人物的相互關系基礎上發生的相對完整的情節。情節設置的優劣,是我們判斷一部劇作優劣的極重要的標準,但我覺得對戲而言,尤其是對戲曲而言,另外一組標準也很重要,就算不能說更加重要,至少同樣重要。這一標準就是,劇本的戲詞是否具有動作性,或者說是否給演員提供了能以動態的方式表演的依據。所謂“劇本”,它的本意,不應該是僅供人們在案頭閱讀的文本,而應該是提供于演員用以舞臺表演的腳本。更明確地說,“戲”,是用來“演”的,好的戲,從大的方面說,它應該能夠激起演員將它搬上舞臺的沖動,從小的方面說,每個局部要充滿有動作性的細節,足以激起演員表演的欲望,叫“有戲可做”。換句話說,演員在臺上是在“做戲”,“怎么做”是演員的事,“做什么”,編劇要負起應負的責任。是否能讓演員在臺上時時感到有“戲”可“做”,就是劇本的優劣標準之一。
戲劇并不是一定只能寫一個故事,即使是寫故事,也需要或可以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人的思想和情感,借此激發欣賞者的興趣,進而打動觀眾。說理,抒情,都是戲劇題中應有之義。但戲劇是在劇場里面對觀眾表演的,觀眾在劇場里真正看到的,只有舞臺上的演員的表演,或者更準確地說,只能通過演員的音聲以及形體,感知戲劇內容。從戲劇效果的角度看,音聲與形體兩方面各有其重要性,我們一直把歐洲人的DRAMA譯成“話劇”,因此容易誤以為“話劇”中最主要的戲劇手段就是演員喋喋不休地“說話”的“話”,然而,事實上,大約除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風行的辭藻夸張華麗的莎士比亞式戲劇以外,就話劇而言,演員的表演,或者說他在舞臺上的表情與肢體動作要顯得更為重要;反而是戲曲,因為大量運用音樂性的手段,音聲的魅力,在某些場合,有可能成為觀眾欣賞的主要內容——恰如人們俗稱的“聽戲”那樣。在昆曲的鼎盛時代,有“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的俗諺,說的就是昆曲李玉《千鐘祿》的“收拾起大好河山一擔裝”和洪升《長生殿》的“不提防余年值亂離”成為被廣泛傳唱的流行音樂,這類著名唱段,已經被人們視為昆曲的標志性符號;同樣,京劇名家余叔巖最為觀眾所津津樂道的,就是他特具風格魅力的唱腔。不過戲曲講究“四功五法”,“唱”、“念”和“做”、“打”不可偏廢,從整體上看,既然是戲劇,表演時的形體手段,始終是最重要的戲劇化的表達。
音聲和形體是戲曲舞臺上用以表情達意最常見和通用的基本媒介,相對于話劇,戲曲更多倚助于音聲這種媒介的情感傳遞與情節推進功能,但身體——包括表情與肢體動作——的表現功能始終不能忽視;而且,音樂的表達過于抽象,假如不能輔之以豐富的形體手段,它的表現力就會大打折扣;在以敘述故事為主旨的戲劇中更是如此,既是以故事的行進為核心,劇情的推進,就必須依靠演員所扮演的人物間多種多樣的互動,讓觀眾具體地感知。越是注重音樂性的演唱,就越是要輔助以充滿動感的形體表演,這是戲劇的辯證法。
這就給戲曲劇本的寫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戲曲劇本的顯要特點,就是它包含大量的唱詞,我們甚至可以把唱詞看成是戲曲劇本最核心的部分。我一直懷疑元代的文人們寫雜劇,四個折子,他們只關心構成“折”的那個套曲,其余的念白,寫也罷,不寫也罷,無可無不可,足可以讓藝人去自己發揮。晚近民間戲曲的演出本,所重也只在唱詞。因此,如果說對于一般的戲劇文本,只需要在通常意義上強調它作為舞臺演出所用的腳本的特征,那么對戲曲劇本,這種特征的強調,更需要體現在唱詞的寫作中。任半塘先生的《詞曲通義》說到戲曲與詩詞在文體上的區別,在于“詞靜而曲動;詞斂而曲放”。從表演上著眼理解他的意思,那我們就找到了曲與詞之本質差異的原因。
但是只看到這一點,是不夠的。戲曲傳統講究的是“聲容并茂”,這既是對演員表演的要求,同時也可以視為對劇本的要求。
如前所述,戲曲劇本必須讓演員“有戲可做”。王國維稱戲曲“以歌舞演故事”,齊如山說國劇“無動不舞”,都用“舞”來形容戲曲中的“做”,多少有些混淆了抽象性的舞蹈和戲曲中“做”的區別,倒是堅持要把戲曲中的“四功五法”改成“五功五法”學者們,清晰地將“做”與“舞”區隔開來。曾永義先生改王國維的戲曲定義為“合歌舞以演故事”,一字之差,有深意焉。戲曲不是歌劇,歌劇追求歌唱演員聲樂藝術水平的展現,所以歌劇旋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唱詞的重要性;戲曲也不是舞劇,舞劇追求的是舞蹈演員抽象的形體韻律。戲曲的歌,是在唱主人公心里所思所想的事情,戲曲的做,做的是戲劇情節發展中的事。戲曲發源于說唱藝術,從說唱(曲藝)發展變化為戲曲的關鍵一步,到就在于從“坐唱”變而為“演唱”,在于戲曲需要“表演”。在所謂“表演”里,歌和舞是相得益彰地融為一體的,假如我們把“歌舞”校正為“唱做”,那么,戲曲演員的唱之與歌劇演員的唱最關鍵的區別,就在于唱時有做;戲曲演員的做之與舞劇演員的舞最關鍵的區別,就在于做所表現的是具體的行為;戲曲演員的做之與話劇演員的做最關鍵的區別,就在于做時可唱。
戲曲唱詞提供給演員用音樂化的方式在舞臺上歌唱,所以唱詞的要義首先是“易唱”,藝人們說的是“張得開嘴”;但按我的理解,所謂戲的唱詞要“張得開嘴”,不只是指演員唱起來是否舒服,更主要是指在唱的時候,身上還能做出來,因為戲曲演員在臺上除了要“唱”,還得“做”。戲曲演員的表演,一邊在口里唱,一邊在身上做,如此才叫做“聲容并茂”。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唱和做兩者應該“合并”為一體,身上做的,正是嘴里唱的,這樣演員才會感到舒服。戲曲的唱與做之間的緊密聯系,至遲在昆曲成熟的時代就已經確立,至今昆曲還保留有大量的“身段譜”,從中足以窺見作為戲曲表演之范本的昆曲,如何通過確保唱詞的動作性,讓音聲與形體之間構成相互映襯的關系。當然,相反的例子也總是有的,李漁推崇元曲,就拿湯顯祖做反面教材,批評湯顯祖的《牡丹亭》那段千古絕唱“裊晴絲吹來閑庭院”和“良辰美景奈何天”,說它“字字俱費經營,字字俱欠明爽,此等妙語,止可作文字觀,不可作傳奇觀也”,除了說詞意失之于晦澀,還可以從另一層意思批評他,那就是,當演員唱到“裊晴絲吹來閑庭院”這句詞,不知道應該用怎樣的動作予以表現?他應該怎么做,才能夠做出“裊晴絲”的模樣,以及“閑庭院”的格局?更不用說“良辰美景”和“奈何天”,這是用來讀的絕妙好辭,卻未見得是用來演的好唱腔。隨手取京劇《武家坡》里王寶釧唱的那段西皮二六:“指著西涼高聲罵,無義的強盜罵幾聲。妻為你不把那相府進,妻為你喪了父女情。既是兒夫將奴賣,誰是那三媒六證的人?”兩相對照,就知道為什么京劇的表演更能吸引觀眾,盡管它的劇本遠沒有昆曲的文采。既然它的發展過程和藝人舞臺上實際的演唱融為一體,唱詞與表演就一定會如此密切相關,唱的和演的,關系再緊密不過。
唱詞如此,道白也是如此。戲曲的音樂性不僅體現在唱的旋律與節奏中,還體現在同樣可以有抑揚頓錯的音樂性的念白里。借用曾永義先生“合歌舞以演故事”的定義,歌舞之“合”,不僅在于唱,而且還在于念白。寫唱詞的時候需要兼顧到演員的表演,寫道白,同樣需要充分考慮到演員在念白時,如何輔之以形體的動作,只有能夠讓演員在舞臺上動起來,戲才是活的。
當然,我們還可以從比較廣義的角度,理解唱詞和念白的動作性。一句“馬來!”的叫頭,固然是可以引出演員一連串的程式化表演的,“一輪明月照窗下”,雖然說的是天象而不是人物的行為,同樣可以表演的,至少給演員提供了人物與月亮之間關系的啟示,既有這關系在,舞臺上的演員,就可以動,戲就如此而成其為戲。
戲曲從文人到民間,流傳既久,即使有時文人創作未必符合演出的要求,經過藝人的改造,也大都不難找到戲與演之間兼而顧之的方法。唱與念等方面動作性的要求,本無需特別強調。可是,20世紀80年代中葉前后,以哲學或思考入戲,一度成為部分編劇的時尚追求,出現了一些貌似深刻的劇本,把舞臺變成了辨論會的會場,表演一翼竟受忽視,舞臺性受到嚴重傷害。更麻煩的是這些劇本與編劇,往往因此暴得大名,后來的編劇,也容易在懵懵懂懂中步其后塵,還以為走在成功的大道上。殊不知戲曲之道,既在于同時發揮音聲與形體兩相結合的情感傳遞的力量,劇本自應該為之創造最佳的條件。寫可以演的戲,才是大路、正路。(來源:搜狐文化-早安京劇)

 關于我們|媒體合作|廣告服務|版權聲明|聯系我們|網站地圖|友情鏈接
| 友鏈申請
關于我們|媒體合作|廣告服務|版權聲明|聯系我們|網站地圖|友情鏈接
| 友鏈申請
甘公網安備 62010002000486號
Copyright©2006-2019中國甘肅在線(甘肅地方門戶網).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