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
是不是情同“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
——作者:郝厚璋
《弘化公主墓志銘》:“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
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渾慕容氏墓志》:“載初元年(690)七月八日,慕容曦光生於靈州之南衙(《光志》)。約是歲前后,弘化公主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公主志》)。[按《志》於此事未系年月。考《通鑒》云:是年八月,武后大殺唐宗室及親黨,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疑弘化公主改號賜姓,亦為是年左右之事。”
意思是,“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時間應該是在690年的“前后”“左右”,原因應該是與千金長公主“更號延安大長公主”的情況差不多。
就因為這一“疑”“前后”“左右”的含糊,近年來“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情同“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的說法比較流行,似乎已經成為“學術公認”“學術定論”。既然“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時間是在690年的“前后”“左右”,就對應690年這一時間點派生出了諸如“690年前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690年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武則天稱帝后,被賜封為弘化大長公主”等等等等的學術觀點。
那么,事實情況是不是這樣的呢?
一、“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與“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完全屬于性質不同的兩碼事
《資治通鑒》:唐睿宗載初元年(690年)“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李賢)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乃)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馀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唐睿宗李旦)姓武氏。太后不許,擢游藝為給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馀人,俱上表如游藝所請,皇帝(唐睿宗李旦)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唐睿宗李旦)及群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數,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圣神皇帝(則天女皇),以皇帝(唐睿宗李旦)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唐中宗李顯)為皇孫。”
幾點常識:
(一)“以唐為周,改元”的時間是,中國農歷690年九月九日壬午。以此為時間界線,此后算大周王朝,此前算大唐王朝。
大唐王朝←690年九月九日壬午→大周王朝
也只有在中國農歷690年九月九日壬午后的武則天才是皇帝。此前的武則天不是皇帝,而是“太后”。故對于九月九日壬午前都清楚地筆之曰“太后愛之”“太后不許”“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請”。
(二)“賜”,皇帝專用詞,其外任何人的任何行為都不能筆之曰“賜”。這是中國古代嚴格的規矩,不管什么類型的文字。
《弘化公主墓志銘》:“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以圣歷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寢疾薨于靈州東衙之私第”。
墓志紀元為大周王朝年號“圣歷元年”,筆之曰“賜”當然是指“以唐為周,改元”后的則天女皇之“賜”。
“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清楚地筆之曰“太后”,時間是在690年九月九日前的“唐睿宗載初元年(690年)八月”。
弘化公主“賜姓曰武”與千金長公主的“改姓武氏”中間隔了“九月九日”一道時間墻,八竿子都打不著。
顯然,所謂“690年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說法屬于對基本常識的違反。
(三)在用詞上,千金長公主筆之曰“改姓武氏”,弘化公主筆之曰“賜姓曰武”。“改姓武氏”是主動式,“賜姓曰武”是被動式。千金長公主是主動要求“改姓武氏”,弘化公主是被動接受“賜姓曰武”。一個是主動當狗,一個是被動接受,做人的格調有著天淵之別。
顯然,“賜姓曰武”根本就不能等同于“改姓武氏”。
(四)“惟”,意即只有這一個,沒有第二個。
“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者,意即“以巧媚得全”的只有千金長公主一人,再沒有第二人。
所謂“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其全部內涵就是,從“唐睿宗載初元年(690年)八月”到“690年九月九日武則天登基稱帝”以至到“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二月甲寅,復國號,依舊為唐”,在李唐宗室成員中,“以巧媚得全”的只有一個千金長公主,再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宗族敗類”。
一個“惟”字界定了,弘化公主的“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與千金長公主的“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乃)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完全屬于情況不同、時間不同、態度不同、性質不同的兩碼事。
(五)《資治通鑒》:天授二年(691年)八月“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馀年。”
所謂“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就是,為了活命,為了進封“大長公主”,不惜背叛李唐宗室,以“自請為太后女,仍(乃)改姓武氏”為手段,為傅游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皇帝(唐睿宗李旦)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為“乙酉,上尊號曰圣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為李唐宗室幾個主要成員“皆賜姓武氏”“皆幽閉宮中”,以至為“除唐宗室屬籍”等等等等帶了個壞頭。這樣的壞人當然得筆之于史,以儆千秋。故《資治通鑒》森然筆之曰:
“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
那些所謂弘化公主的“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情同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的類類論調,意即弘化公主行如千金長公主的“自請為太后女,仍(乃)改姓武氏”,通過求得“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才得以“巧媚得全”,是帶頭促成“改姓武氏”的罪魁禍首,與千金長公主同屬于不齒于人的一丘之貉,人格之下作豬狗不如。
有這樣糟蹋一個古人的嗎?
二、是不是“武則天稱帝后,被賜封為弘化大長公主”?
所謂“武則天稱帝后,被賜封為弘化大長公主”,意即進封“弘化大長公主”的時間是在“武則天稱帝后”的690年及稍后。
《弘化公主墓志銘》自前而后語句順序:
“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 →“即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也” →“大長公主,誕靈帝女” →“以貞觀十七年出降于”→“我大周以曾沙紉地,練石張天” →“主乃賜同圣族,改號西平”。
(一)“即大唐”,確定是指大唐王朝(中國農歷690年九月九日前)。“我大周”,確定是指大周王朝(690-705年)。
(二)墓志正文“主乃賜同圣族,改號西平”排在“我大周”之后,確定“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時間是在690年武則天稱帝后。
(三)墓志正文“大長公主”一詞排在“我大周”之前,確定進封“大長公主”的時間是在“即大唐”期間,而不是在“我大周”期間。
(四)因為“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時間是在“我大周”期間,確定墓志正文“大長公主”一詞是指進封“弘化大長公主”的時間,即在“即大唐”期間。
查,唐中宗第一次在位實際時間粗計兩個月(683年十二月-684年二月)。按輩分對應和時間許可推算,確定進封“弘化大長公主”這一封號的時間是在唐睿宗李旦第一次在位期間(684-690年)。
顯然,所謂“武則天稱帝后,被賜封為弘化大長公主”是不能夠成立的。
三、“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時間是不是690年?
(一)“弘化大長公主”這一封號在“我大周”期間延續使用了足夠長時間
1、《弘化公主墓志銘》墓志題頭“大周故”三個字限定了,“大周故”之后所列官號皆為“我大周”期間使用官號。
武則天登基稱帝“以唐為周”,就是改朝換代。官號是一個王朝的重要標識,廢止前朝官號排在改朝換代的當先序列。墓志規矩,前朝官號不得列入墓志題頭,但在墓志正文中的敘述不限。亦即,列入墓志題頭的必須是本朝官號,這是中國歷朝絲毫不能含糊的政治規矩。
2、墓志題頭“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弘化大長公主”明確列在“大周故”三個字后面,確定“弘化大長公主”為“我大周”期間延續使用的封號,且以“大周故”意在突出強調在“我大周”期間續用了足夠長時間。所謂足夠長時間,就不是幾個月,也不是一年兩年。按照墓志規矩,如果續用時間不是足夠長就會略而不入墓志題頭,而是放在墓志正文中敘述。這是必須的“講政治”,可以翻查任一官方墓志去對證。
如果“弘化大長公主”這一封號在“我大周”期間延續使用時間不是足夠長,墓志題頭就會寫作“大周故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而把“弘化大長公主”這一封號放在墓志正文中敘述,意思同樣完整。這是撰寫墓志的基本常識。
3、《舊唐書》:“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按照唐朝喪葬制度,一品人物的墓志歸“皇家宮廷制造”,《弘化公主墓志銘》類屬“皇家官定墓志”。
《弘化公主墓志銘》:“成均進士云騎尉吳興姚略撰”。查吐谷渾墓志,這行字為《弘化公主墓志銘》獨有。詳查唐朝墓志,“官銜+署名”代表一種最高禮制規格,這是高品級人物“官方墓志”的重要標識,也代表皇帝的特別恩典。除了“奉敕撰”外,不是高品級人物墓志上無資格配享這行字。
毫不含糊,“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并不是隨便寫入墓志題頭的。
4、一言概之,“弘化大長公主”這一封號為前唐睿宗李旦第一次在位期間進封,在大周王朝期間延續使用了足夠長時間,直至啟用新封號“西平大長公主”的同時被廢止。
(二)扣除掉“弘化大長公主”這一封號的延續使用時間,“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時間就不可能在690年
《弘化公主墓志銘》:
“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
很清楚,“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時間是在“弘化大長公主”之后。
“(690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改元為天授(690年)”,從“九月九日”到年臘三十日690年全部結束,690年還剩幾個月?
顯然,扣除掉“弘化大長公主”這一封號的延續使用時間,“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的時間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690年。
四、“賜姓曰武”只與“西平大長公主”有關系
《弘化公主墓志銘》:
“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
這一先后排列次序清楚地點明,“弘化大長公主”姓“李氏”,只有“西平大長公主”才姓“武”。也就是,“賜姓曰武”只與“西平大長公主”有關系,與“弘化大長公主”沒有關系。把“賜姓曰武”與“弘化大長公主”攪雜在一起是錯誤的。
總之,解讀《弘化公主墓志銘》的要害有二:一個是墓志正文“大長公主”一詞的位置,這是確定“弘化大長公主”這一封號進封時間的明確標識。一個是墓志題頭“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這是界定弘化公主封號時序的關鍵點所在。在弘化公主封號問題上的錯誤解讀,無不源自對于這兩個要害的錯誤理解。
(2023年11月3日開筆,2023年11月4日終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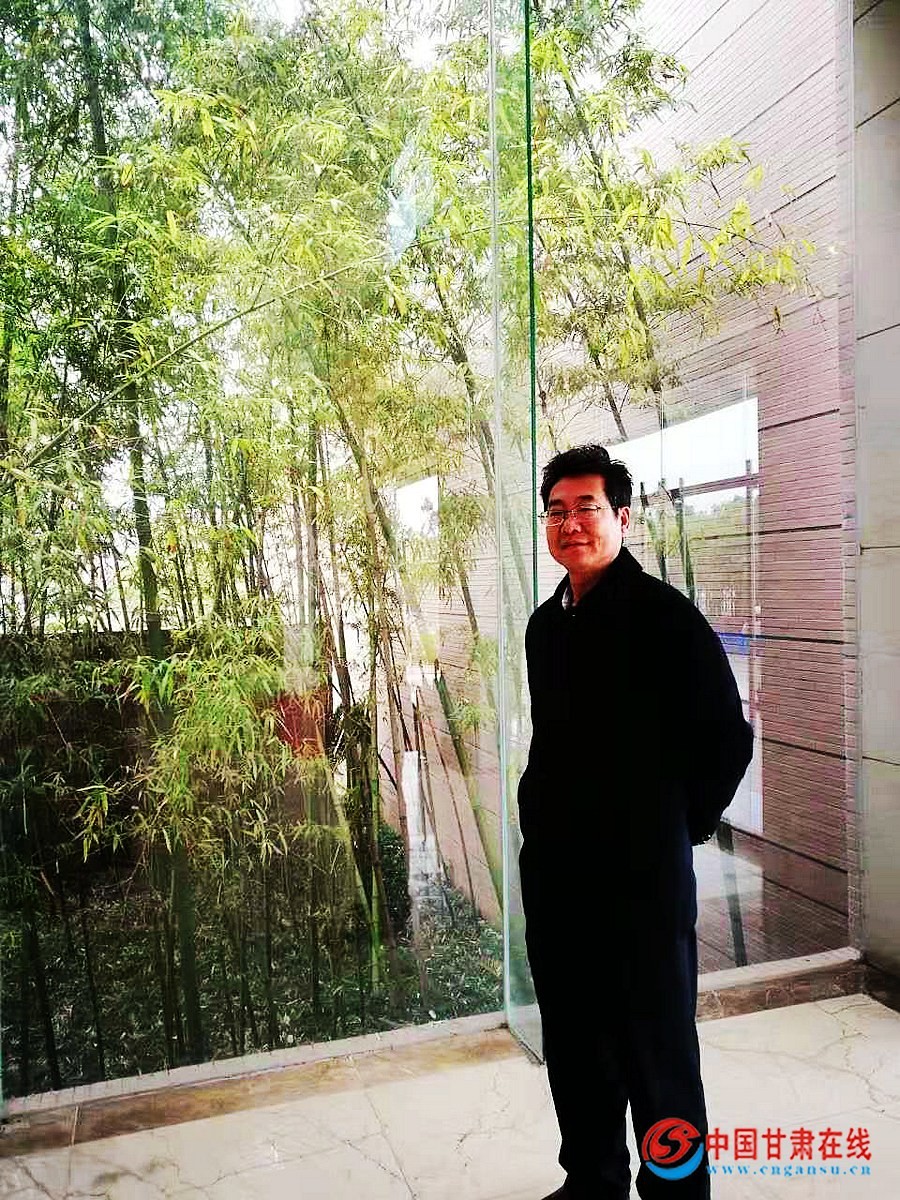
作者簡介:郝厚璋,生于涼州,學于蘭州,居于福州。文學作品發表于《中華時報》《讀者》及新華網、廣播電臺等刊物媒體。經濟社會研究成果發表于《新華文摘》《人民文摘》《國內動態清樣》《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等刊物。

 關于我們|媒體合作|廣告服務|版權聲明|聯系我們|網站地圖|友情鏈接
| 友鏈申請
關于我們|媒體合作|廣告服務|版權聲明|聯系我們|網站地圖|友情鏈接
| 友鏈申請
甘公網安備 62010002000486號
Copyright©2006-2019中國甘肅在線(甘肅地方門戶網).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