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漢后來回憶說:“在到哈達鋪前,在河邊的一個圩場上,我看見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等同志一起休息。毛澤東向我打招呼:羅邁,你也來休息一下!我就下馬休息,看到他們正在翻閱一張國民黨的地方報紙,上面登了蔣介石大軍圍剿陜北“共匪”劉志丹的消息。我們才得知有這樣大的紅軍在陜北蘇區積極活動,黨中央隨即決定到陜北蘇區與陜北紅軍會師。”
在哈達鋪,中央紅軍由“一張報紙”定去向、定落腳點,看起來是“偶然”的,甚至是難以置信的,實則是“必然”的,這恰好反映了毛澤東同志胸懷大局、高贍遠矚,對
中國工農紅軍的發展前途和
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方向洞若觀火的遠見卓識。早在1931年日本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毛澤東就敏銳地覺察到,這一嚴重事件,將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國內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隨即與朱德、賀龍、彭德懷等聯名發表了《
中國工農紅軍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州而告白軍士兵兄弟書》的文章,主張聯合起來,堅決抗日。但這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他們根本不能正確地估量全國局勢中出現的這種重大變動,而把日本侵占東北看作是“反蘇戰爭的導火索”,脫離實際地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看不到
中國社會各階層中日益高漲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間派的積極變化和國民黨內部的分化,仍然把中問派視為“最危險的敵人”。
1932年初,毛澤東從報上看到日本軍隊1月28日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的消息,他抱病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民族矛盾引發階段矛盾的變化、對民族革命推動民主革命的進程,對外來勢力入侵促成全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早有高瞻遠矚。這也是他在長征途中為什么總是義無反顧地引導紅軍堅持“北進”方向,堅持“北上抗日”方針的原因所在。如果說,黎平會議、遵義會議和兩河口會議解決了紅軍長征途中的“定向”問題的話,那么,哈達鋪會議不僅解決了“定向”的問題,而且解決了“定點”的問題。因此,哈達鋪會議雖然沒有冠以“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名,卻具有 “重大轉折意義”之實;雖然沒有形成正式的文字性決議,卻為紅軍長征解決了最后的歸宿問題。哈達鋪會議的歷史意義和作用毫不亞于黎平會議、兩河口會議和毛兒蓋、俄界等會議,在中共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從1935年9月18日占領哈達鋪到9月23日,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在哈達鋪僅僅呆了5天(加后繼部隊為7天)。在這短暫的5天內,黨中央進行了著名的“哈達鋪整編”,給紅軍將士從體力上、生活上、物質上、精神上和部隊編制上進行了全方位的“加油”與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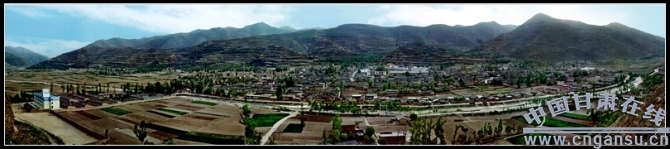



 關于我們|媒體合作|廣告服務|版權聲明|聯系我們|網站地圖|友情鏈接
| 友鏈申請
關于我們|媒體合作|廣告服務|版權聲明|聯系我們|網站地圖|友情鏈接
| 友鏈申請